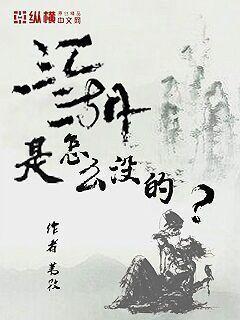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章 九枚银币(第2页)
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这场冲突里没有恶意十足的殴打取乐,没有侮辱性强烈的话语挑衅,甚至不存在任何有效交流。
这只是一段麻木的工作。受困于贫苦的人群相互抱团,结成帮派,把一些两脚羊绑去卖掉,换取钱财,提供一家人吃住的同时,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有罪。
在许多故事中,加害者总是特殊的,要么有着扭曲的心理疾病,要么有着饱受创伤的过去,以致于,受害者在他们眼里也会是特殊的。他们往往会在施加暴行时长篇大论讨论作恶的原委,受害者想要和他们谈多久,就能和他们谈多久,受害者想问什么问题,他们就会配合地回答什么问题。
然而从更广泛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加害者只是在做些麻木的工作,把受害者看成工作中要处理的货物,塞恩伯爵怎样,他不知道,但这些结成帮派的搬运工都是如此。当他们和自己人谈话时,通常是交好的朋友、是亲切的长辈、是辛劳的父母,一旦走出这个范畴,他们就会在一个不存在道德的领域里做出自己只当是搬运货物的行当。
把人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大致上也能算是种搬运工。
看到巷口的小孩还没走,两侧楼上也有人在窗户后面偷偷张望,塞萨尔发现这地方已经吸引太多目光了。身为在逃犯人,有些事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他用自己过去的语言吩咐狗子按捺情绪,等到了足够偏僻的地方再看情况。
她笑得很开心,并且在不久后变得更开心了,就像一个不明世事的傻女孩,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不过,对一个被血肉之欲填满的孽怪来说,明了世事也没什么必要就是。她开心的理由也和人类不太一样,就目前情况来看,其中包含了很多残忍嗜虐的意味。
。。。。。。。
五个搬运工环绕着他们俩走过一条条巷道,其中不乏塞萨尔也毫无印象的小路。他本以为自己对下城区足够了解了,现在看来,他的见识和本地人还是差了很远。这一路走下来,感觉像是找了五个本地向导给他领路,介绍城里的隐秘场所,还贴心为他挡住了刺骨寒风。
不能怪他缺乏紧张感,只是这五个搬运工除了面相凶恶,实际威慑力还不如白眼一条胳膊。
氤氲的湿气充斥巷弄,坠得空气沉甸甸的,呼吸起来,感觉自己像是裹在浸了污水的脏被褥里。有那么一阵子,塞萨尔觉得附近在下雪,不过,仔细看能分辨出,只是煤灰和烟霭四处弥漫,和港口的潮气汇合在一起,一度像是大雪在飘。
当搬运工把他们推到一座四面围得密不透风的院落前时,他意识到,这五个人不过是人口贩卖链条的第一环。少了两根手指的搬运工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脚手架,敲了敲二层的窗户,然后往他们带来的女孩一指。至于塞萨尔,他可能只是附送的壮劳力,可以干点脏活累活。
他们和二楼窗背后的人谈条件时,塞萨尔不由得想到,既然要把他当添头来议价,他们干嘛还要把他俩拉开呢?难道就是走个流程吗?因为懂行的人只教了他们该这么做,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可以有变通?
可能的理由很多,但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细节,思来想去也没什么意义。刚想等这边事了,他却看到窗户那边的人扔出来九枚银币。虽不知九枚银币的估价算不算贵,但是,倘若搬运工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帮派,只是小团体结伙,合谋做事,彼此之前没有地位差别,那么,这九枚银币是不是不够五个人均分?
事实确实如此,很快,低声商议就被搬运工们狂躁的大喊给盖住了,狗子眨眨眼,不明所以地看着两边吵了起来。那些搬运工对他很沉默,这时候却表现出了各自飞快的语速,污言秽语不断,反复强调九枚银币没法给五个人平均分,所以,他们要求看在附送品的份上多给一枚。
窗那边的人也喊了几句,说,塞萨尔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钱,如果给了钱,岂不是去狗坑附近随便绑个矿工过来,也能值一枚银币了?
搬运工们根本不服理,于是越发狂躁了,叫喊声也逐渐变成咆哮。那个脸颊烧伤的搬运工直接对着架子一蹦,就像条猿猴似的爬了上去。他那张烧伤一半的嘴不停开合,像是患了癫痫,唾沫星子像大雨一样喷到二层布满烟灰的窗户上。
身为受害者,塞萨尔其实不该拿这事当乐子看,但这事确实难得一见,他很难不报以好奇心。
“闭嘴,挑大粪的!”窗户那边的人也喊道,“你们他妈的叫什么?这可是卡萨尔帝国铸的银币,你们他妈的不会自己看着分吗?”
“你这妖魔,瘸狗,赖皮猪!”脸颊烧伤的搬运工对着窗户狂嚎道,“你在胡说什么?你知道我们不认识这些钱,难道你还要让我们去找兑币商让他赚差价?他要是说卡萨尔帝国已经完蛋了压我们的价,我们能怎么办?”
“你不就一个搬垃圾的?你能知道什么?”
“你说什么?你侮辱我!我要杀你老娘,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这种拿分不了的钱欺压我们辛苦养家的人的畜生知道什么叫良心!”
“你们也他妈的配谈良心?”
“坐椅子上的瘸狗!老不死的杂种!”底下的搬运工也提高了粗嗓门,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就知道偷鸡摸狗收好处费,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以前搞残了要卖好价的货色害的人没卖出去,只能在港口拉客吗?你的那点破事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窗户那边的人几乎是恼羞成怒了:“你敢在这里造我的谣?闭上你的狗嘴,挑大粪的畜生,小心我拿鞭子把你抽得满地乱滚,驾着马车把你压成两截,我把你和你的——”
搬运工们嚎得更难听了,声音也把窗户那边的人盖了过去,污言秽语越来越难听,但没有像当时一样吸引很多人从窗户背后窥探。照这么看,这附近的建筑里可能都是他们的人,规矩很严格,已经称得上是某种大型帮派了。
就在这时,终于有三个人推开院落门走了出来,看起来是打手。他们身上的衣服虽谈不上富有或花哨,但能显出比狗坑的居民都高一个社会阶层。带头那人挥挥手,示意搬运工们稍安勿躁。
此人话语的说服力明显来自他身后两名黑帮打手。那身加厚的黑色硬皮革马甲看着颇具防护力,一柄钉头锤和一把锋利的单手斧也说明他们来者不善。
搬运工们的污言秽语稍微低落了点,缺了手指的那位还在大声抱怨,但看到来人,他还是从二层跳了下去。往下跳的时候,脸上带疤的搬运工仍不忘朝窗缝里扔了块石头,砸在木头家具上发出了咣当响声。
虽然很想知道他们要怎么平息冲突,不过,打手已经在把他们俩往铺满煤渣的院落里推了,不值钱的塞萨尔和进价两枚铜子转手价九枚银币的狗子也只能进去。
院落没什么稀奇,但被推进一侧的房子后,塞萨尔发现里面弥漫着滚滚烟雾,——不是呛人的炊烟,是种甜腻黏稠的怪烟。他捏了捏嗓子,觉得喉咙不舒服,眼睛也受了些刺激。这地方又昏暗又宁静,光线都是从壁挂的彩色盏灯里射出的,各种斑驳的图案投在墙上,各种不同的色彩互相交错,给人的感受极其迷幻。
穿过走廊时,塞萨尔看到有人掀起脏污的帘子,进了一侧的房间。通过那片刻时间,他看到昏暗中许多人瘫在一张张木头大床上,大多都衣衫不整,意识不清,周身环绕在缭绕的烟雾中,显得一片颓废。
虽然这地方位于下诺依恩,靠近狗坑的贫民窟,但这些客人都衣着华贵。有的客人身旁抱着同性异性皆有的伴侣,但大多数客人都只是享受着环绕周身的烟雾,时不时身体抽搐两下,发出怪声,看着像是陷入了某种怪诞的白日幻梦。
这地方的氛围阴暗又诡异。
三小无猜
狭窄的巷子里,气氛暧昧。烟雾缭绕间,校花被那个皮肤冷白的少年摁在墙边。月光照着他眼下那颗泪痣,性感撩拨。校花娇羞地说那边有人。祁浪回头扫了眼身后那个来给他送腊肉有点不知所措的女孩,意态慵懒哦,我...
暴君乖乖,小姐姐疼你!
沈之乔被另寻新欢的夫君休弃,无家可归。心狠手辣的小暴君却忽然找上了她,救命之恩,朕要以身相许!沈之乔不不不,你不想小暴君朕可以帮你虐渣男贱女,灭他全家!沈之乔容我考虑一下小暴君皇后之位,倾国以聘,我此一生只爱你一人。沈之乔!!!还考虑个毛线,小暴君,来姐姐疼你!...
开局女帝做正宫
...
夫人被迫种地后开始撩汉
人人都说京城贺家大小姐贺妙妙在穷乡僻壤长大,是个乡野村姑,粗俗不堪,与贺家收养的二小姐完全不能比。她回到贺家后非要买一栋别墅专门种地,引来无数嘲笑。对此贺妙妙不屑一顾,怒我直言,在座各位都是垃圾,比不上我园里的一根草有价值。众人切了一声,你除了贪财好色,有霍少撑腰,还有什么?霍璟辞一把搂住贺妙妙的腰,怎么?本少爷就喜欢被她贪财被她好色,你们有意见?众人怂,敢怒不敢言。之后大家看见贺妙妙成绩班级排名第一,高考成了全国状元,玩个游戏轻松打上了国服,地里的草能救人性命众人嘴角抽搐,这打脸还能再来几下吗?...
江湖是怎么没的
一个低情商,一个真小人,却阴差阳错成了武林盟主。朝廷中暗流涌动,江湖上风云变幻,一场阴谋布局之下,看俩逗逼如何祸乱江湖!...
超级狂婿
入赘两年,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废物,可以将他踩在脚底下,直到离婚那天,才知道,他竟然富可敌国,权倾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