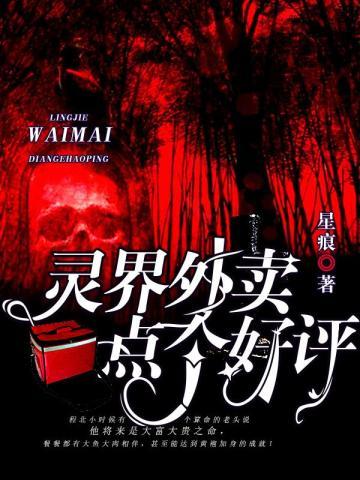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风雪库热西(第1页)
刚到哨卡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漆黑冰冷的空库房里过夜,等待着退伍老兵第二天走后,给我们腾出来一手臂宽的通铺。别的部队新兵没有到之前,老兵就可以退伍,边防哨卡的老兵却要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能让新老接替之间出现断档。哨卡没有多余的铺位,我们只有睡在库房冰冷的地上。
这虽在3月,明铁盖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库房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像冰窖。地上连一把干马草也没有,我不忍心把被子铺在地上,就裹紧皮大衣,打算坐在背包上熬过这一夜。像我一样坐在背包上的还有三个人,他们是三个维吾尔族兵,叫买买提、沙地克和库尔班。在新兵集训连,他们在维吾尔族班训练,我认识他们,但不太熟悉。这会,他们挤在一起卷莫合烟抽,用维吾尔语交谈。我还没有习惯莫合烟,它有一种马草的味道,有一种草地空气的清新味道,不像别的烟那样呛人。我喜欢那点在他们腮边忽明忽暗的烟火光,它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夜很冷,有几个睡在地上的战士又爬起来了。一个哨兵踱进屋来,对三个维吾尔族新兵说:“把烟灭掉,这是边防,夜间不准抽烟。”我后来知道他叫詹河,是个河北兵。他出去后,屋里又是三个维吾尔族新兵在说话。不一会,一道手电光照进来,三个维吾尔族新兵都把头抬起来。进来的是两个维吾尔族老兵,我后来知道他们一个叫库热西,一个叫阿不拉提。
他俩叽叽咕咕和三个维吾尔族新兵交谈,又轻轻笑出声来。几个维吾尔族兵又都把莫合烟点上。我猜测:两个维吾尔族老兵刚才是在笑话詹河,说他在吓唬新兵。个子瘦高的阿不拉提很快出去了,他从自己宿舍里抱来一条毡毯、一床褥子,帮助三个维吾尔族新兵打地铺。
我坐在背包上打盹,后半夜困倦地歪倒在背包上。
第二天,退伍老兵要走了,他们要把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用品给我们留下。而有朝一日,当我们告别哨卡时,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向我们的接替者再传下去,美其名曰“送传统”。一个湖北老兵把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碗、一双筷子和一只有点瘪的脸盆传给我。我以后就要用这些家什吃饭洗脸了。我的高山反应还没有过去,木讷地竟忘了和他说句谢谢。而他像失了魂似的,脚下踉跄着,匆匆爬上停在哨卡营区大门外的大卡车。一阵锣鼓家什敲响,他们被送走了。
他那样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在几年后退伍时才深刻理解。
当天,我被分在三班。我的铺位紧挨着阿不拉提的铺位,他是一个很和气的人,瘦高个,刀条脸,稀疏的浅色头发,稀淡的倒挂眉,走起路来松松垮垮。他每天在我的前面上夜哨,推我起来上夜哨时,他的身上从屋外带回来寒气。他的汉语说得很差,往往从他这里开始,口令就传错了。比如说,口令本来是“食堂”,当他传给我时,他要想一想,结果就传成“稀饭”了。这是很危险的,如果真有人通过哨卡进入边境禁区,对错了口令,我们就要开枪。到后来,我知道阿不拉提有这方面的缺陷,每次接到他传的口令,都要把他前面的那一个哨兵推醒来进行核实。
不过,我很快就调离三班到连部去了,阿不拉提就再也没有向我交班的机会了。
我到连部接手文书职责。
每天晚上,头一班哨兵都要到我这里领口令。如果来的是维吾尔族兵,我一定要反复叮咛,口令一定不可传错,或者在他的下一班进行抽查,看他传出去的口令准不准。
在维吾尔族兵中,比较让人放心的是库热西这个人。
库热西原是一名机枪手,在我到哨卡时,刚刚被宣布为二班副班长。他中上等个头,体魄健壮,宽肩,倒三角体形,运动时喜欢把袖子和裤腿卷起来,露出粗壮的胳膊和有力的腿;红脸,宽颧骨,稍微卷曲的栗色头发;眉骨耸起,眉毛淡而稀疏;有点凹陷下去的略带棕色的眼睛;粗鼻子,阔嘴,整齐的牙齿,下巴结实。
在篮球场上,他凭着体格强健横冲直撞,简直像一辆坦克。而且他眼露凶光,咄咄逼人。
他说:“我的名字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斗争。”他打篮球时就表现出那么一种气势。
5月,连队借来犁和牦牛,在河边翻地种青稞。由于高寒,这片青稞不可能结籽,但它收割后可以晾晒成干马草,储存起来供马匹过冬。坚硬的冻土,犁起来很费劲。高原犁地是“二牛抬杠”,两头牛颈上架一根杠子,同拉一张犁,就这样,牛还累得直喘气。一头牛累趴下了,库热西一急,脱掉棉袄,和另一头牛一起拉犁。他的力气比牛的还大,把牛拉滚到一边。
7月,我们到卡拉其古一带打柴。在乱石密布的山坡上,寻找一种被碎石掩埋在底下的松树。我们一般都沿着山沟往沟里走,到石坡上挖掘,把埋在石堆下的松树挖出来,再拖下山坡。库热西却带着几名维吾尔族兵去攀爬绝壁。绝壁上,星星点点的有那么几棵树。他们在绝壁上把树放倒,让树从高空落下去。看着他在悬崖上攀爬,把身体紧贴山崖,呈一个“大”
字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汗。
库热西是识马的好手。去喀什领军马,一路风餐露宿,一连十天,一路观察那些马,给相中的马做记号,想着留给自己的连队。在分马时,他和九连的一名维吾尔族兵翻脸,双方对骂,动了鞭子。那兵在马群经过明铁盖时飞身上马,把一匹乌龙马抢了去。看着那小子骑马飞越过雪冈,库热西气得双脚直跳,两眼充血。
他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人,却梦想着提干长期留在哨卡,当一名翻译。
他懂一点汉语,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常常煞有介事地捧着维吾尔文本《毛选》(第五卷)阅读,并且在大会的发言中引用。他用维吾尔语念一遍后再用汉语解释,以证实他的水平。
他很快入了党。
他决心抓住机会,来一个突破,机会稍纵即逝嘛!他幼稚地打破自己的民族习俗,以证实自己的“进步”。他原本是一个穆斯林。他这种幼稚的做法,却招来别的维吾尔族战士的愤怒。
“库热西妈妈的!”买买提说。买买提原本很尊敬库热西,现在却轻蔑地朝他背后啐口水。他得罪了别的维吾尔族兵,一时间变成孤家寡人。
下一年春天刚过,团里突然给哨卡派来一名翻译,翻译叫依米提。依米提脾气好,处事沉稳。依米提的汉话并不比库热西讲得好,但他会写汉字。库热西是那种一有心事就表现到脸上的人,他的失落很快表现到脸上来。只不过一两天,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民族习惯,因此,也恢复了维吾尔族兵对他的尊重。
6月份,库热西回去探了一次家。到了9月,他又要求下山到塔什库尔干看病。哨卡人很快知道了他的秘密,原来,库热西在塔什库尔干与一名塔吉克族干部的女儿谈婚。
“库热西妈妈的!”买买提又愤怒地说。
买买提是一名粗汉,健壮、结实,满脸浓密的络腮胡子,有两片乌鸦羽毛一样粗而乌黑的眉,乒乓球一样大的眼睛,大鼻子。他看去很凶悍,实则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非常细腻,又非常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童心男子,和我是朋友。
买买提认为,库热西的婚姻目的不纯。他说:“他是为了在塔什库尔干安排个工作!”
果然如此。次年春天,库热西退伍,很快在塔什库尔干和女友完婚,又很快安排了工作,却是在离县城一百公里的卡拉其古牧场当一名牧工。这单位就在我们营部驻地附近。
这年5月,库热西忽然回到明铁盖哨卡来了。他带着一辆吉普车。大家都“库热西,库热西”地叫,围上去。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卡其中山装,绿军裤。他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与他同来的还有牧场的两名维吾尔族职工。
那年月粮食紧缺,库热西回哨卡是想买一些面粉。他一定给牧场的人吹过牛了。在过去,在古尔邦节或肉孜节,他必定和哨卡干部一起,带着面粉、盐巴到老牧民热孜克家慰问。他估计买一点面粉不成问题。
库热西爽朗地向连长开口。
“库热西想买面粉。”连长说。
副指导员刚从司务长职务上提起来,瞅着库热西笑,笑过之后说:“库热西,你不是退伍了吗?”
锦鲤特工在种田
穿成被无良叔婶卖给人牙子的八岁小孤女怎么办?雇佣兵出身的聂绾绾表示不怕不怕,开局先分个家!然后再当个小大夫,开个小酒楼,买座小玉山,发家致富就在眼前!去前线的大哥回来了,失踪的父母也回来了,还有个小狼狗整天围着她打转!小日子渐渐滋润起来,聂绾绾觉得自己有亿点点优秀!生活有亿点点幸福!并且想躺平摆烂可小狼狗丈夫却直勾勾地盯着她平坦的肚子媳妇儿,还要再生个小狼崽儿才能躺平!一二三四五,六六聂绾绾数着满屋子蹦跶的小狼崽,一脚将跃跃欲试的某男踹下炕。...
灵界外卖,点个好评
程北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老头说他将来是大富大贵之命,餐餐都有大鱼大肉相伴,甚至能达到黄袍加身的成就!没想到竟成了外卖配送员,一天,一个配送费200元的天价订单,将他牵扯进了十年前的一桩悬案中是无情的地狱,还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逃亡游戏:我被全人类通缉了
林季瞎了后,为治疗在医院住了十三年。意外激活系统后,他重获光明。却发现,他接受的根本不是治疗,是囚禁。甚至,有人说他是个天才罪犯,罪大恶极。他想出逃,想查明真相。可系统却反复叮嘱他别让他们知道,你看得见。他不解,被发现了会怎么样?会死。...
王爷,王妃貌美还克夫
林卿嫣命太硬,三年克死了六个丈夫,一朝国破,她替妹妹和亲,被送上敌国的花轿。所有人都等着她把他克死,谁知他不仅没死,最后还成了九五之尊,而她成了他掌心里的娇宠。可她却只想逃,因为他太恐怖,手段太残忍。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的把她拎入怀,声音凉薄再跑,腿打断!她你看你看,果然很凶残...
田园小吃货:怀着包子去致富
沈竹不仅穿越了,还怀孕了!什么?这家里的人食不果腹还有极品亲戚打秋风?那就打回去!谁知,身边男人摇身一变,成了尚书。沈竹觉得还是保命要紧。婆婆要给自家男人纳妾巩固实力?还是当初指腹为婚的人?沈竹嗯,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只见男人阴沉的脸色一转,娘子,做什么?额,朋友两字怎么那么难说出口。...
福宝团宠:神医娘亲开挂了
风寄灵,一朝穿越成了被毒哑被下药的侍郎府小姐,性如烈火的她,怎肯任人摆布,太监了狗男人,火烧宅院,搅得人仰马翻后,一个不注意,滚落山涧。送上门的美少年,正好用来解药。一夜情浓,风寄灵竟凭空消失了。五年后,为了一株宝药,二人再次相遇。彼时,美少年成了位高权重的王爷,豆芽菜少女成了单亲带娃的女医。王爷,你这长相,丑帅丑帅的,要不要我给你做个微调。某王爷冷笑,撕掉脸上的面具,抱起身旁的小崽子。现在再看看,是本王帅,还是我们的儿子帅?...